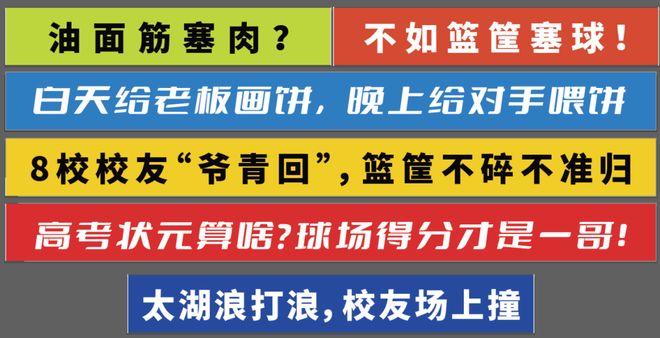回到七年前的一个夏夜,李星在朋友组织的攀岩聚会上认识了大学讲师张雪。在李星的记忆中,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张雪是少女模样,笑吟吟地,打量着迟到的自己,好像很好奇。暑气弥漫的北京一下子变得黑白分明,让李星心里咯噔一声,觉得这辈子就是她了。
后来,李星每周末都会约张雪出来玩。最初两次,也会精心设计路线和项目,邀几个朋友。又过几个月,张雪不再拘谨,两人就是简单地看个电影,或者去游乐场玩过山车,最后去环境好些的餐厅吃顿晚饭。那时李星三十岁出头,北京金领,月薪四万,这些消费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和张雪在一起,花钱时有快感,空气都是甜的。有天晚上,两人吃完饭,李星把张雪送到她家楼下,张雪下车时突然回头想了想,慢慢说:“以后咱俩不用吃这么贵的饭,咱省出钱来,干点什么不好呢。”
张雪在学校主讲心理学,说话很有水平,李星每次都要拐好几个弯才能猜出来她的真意。张雪下车之后,李星忐忑了半小时,给几个要好的朋友都打去电话,确认了张雪已经把自己当作利益共同体之后,在车里听着歌傻笑了二十分钟。
又过了半年,张雪成了李星的新娘。婚礼上,穿婚纱的张雪美得让李星鼻尖发酸。两人动用了全部的积蓄,在东五环外买了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装修和布置完全按照张雪的意思。住进去的第一天,两人站在大落地窗前,看到不远处的一片树林中有小鸟在枝头蹦跳。张雪说:“这是不是我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候?”李星说:“只会越来越好。”
如今在去往草原的路上,李星再回忆起那个时刻,百感交集。“越来越好”,这曾经的雄心壮志被现实击成粉末。张雪最早发现暖阳不对,是因为这孩子从不会在拉屎前像同龄人一样哇哇大叫或手舞足蹈,他想拉就拉。家里到处都是污渍,张雪那些精心的布置在暖阳的屎里看着就像个笑话。李星一直不愿承认儿子有问题,直到暖阳两岁,李星扛不住了。当那个戴无边框眼镜的医生对李星夫妻平静地说出“自闭症”这个词时。张雪一下子就哭出了声,李星紧握着拳头,却不知道这拳该挥向哪里。他咬牙,心一阵一阵揪着痛。
李星听到车厢外的叫声,他睁开眼,儿子一直坐在自己的身边,静静看着自己。李星亲亲暖阳的额头,那一刻他感到儿子的心跳有力得如同一头小小的野兽,却又和自己的心跳同频。这让李星觉得无比温暖,一切都有了意义,无论接下来要去哪里,要发生什么。他轻轻握住了儿子的手。
在天那边的草原上,年轻的牧民宝音正驾车疾驰。他开着一辆快要散架的皮卡车,喇叭里正在播放一首老歌,是一个女人唱给恋人的。在歌里,女人向恋人发誓,即使所有的星星陨落,即使银河系熄灭,她也会忠贞不渝,守护爱情。宝音戴着口罩,跟随那女人的唱腔鬼哭狼号。宝音喜欢这首歌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这首歌里有关于宇宙的描述。在这里,就连孩子都知道,宝音是草原上最热爱宇宙的牧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个宇航员。连巴桑都不明白,他这股劲头究竟从哪里来。
皮卡车驶到了草场上,几座毡包相连,宝音跳了下来。挤奶的女人们和劈柴的男人们看着他,眼神里有些厌恶,像是看到了狐狸。宝音不理会这些,微笑着对每个人说:“嘉(你们好啊)!嘉!”
没人理他。宝音很尴尬。他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向一个哇哇大哭的小胖子扔石子,于是他走了过去。那些顽童并不惧怕宝音,用鼻孔对着他,脸上挂满冷笑。宝音也不说话,猛地摘口罩,怪叫一声。
宝音的左半边脸在八岁时烧伤了,如今疤痕密布,没有脸皮,褐色的肌肉像一条条虫子般扭曲在一起。他看上去就像个鬼。孩子们被吓跑了,宝音嘿嘿笑着。想把那个小胖子扶起来,可没想到小胖子哭得更厉害了。宝音急忙用口罩遮住面孔,小胖子说:“叔叔你让我走吧,别把我吃了。”宝音咬牙,挥挥手说:“滚滚滚。”小胖子连滚带爬,回到了那群朝他丢石子的玩伴当中。
宝音一阵懊恼,挠挠头说不认好赖人。草场的男主人放下斧子,用毛巾擦擦汗。他说:“宝音,你还是这样。一个牧民没牲口没草场,不是好男人。”宝音嘿嘿傻笑,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糟糕透顶的风评。男牧民说:“要不,你来我的草场吧,帮我放羊吧。我给你羊羔和奶牛做工钱,过不久你就能成个家,怎么样?”宝音说:“太空在等着我,前段时间上面下来通知了,我就快去做宇航员了,谁给你留在这儿做羊倌。”牧民的妻子撇撇嘴道:“人家宝总是干大事的,咱这破草甸子人看不上……”
宝音冷笑着走了。
宝音不知道,巴桑带着李星一家正在心急火燎赶往草原寻找自己。一路上除去上厕所,这行人没有歇息过。到了晚上,璀璨的群星刺穿天幕,他们已经来到了草原的腹地。草的影子在月光下飘浮在空中,仿佛深海中的鱼群一般划过。
巴桑骑着马疾驰,蜿蜒的公路伸向了天的尽头。越野车在后面跟着巴桑。李星踩了脚油门,车赶了上去,与马并行。这时车厢里的暖阳突然激动地把手伸向窗户,大声哭号着。李星吼道:“他怎么了?”张雪懊恼道:“不知道啊。”就在这对父母一筹莫展的时候,巴桑示意张雪摇下车窗。巴桑骑着马靠过去,暖阳笑了,伸出手摸摸那匹马肥硕的屁股。马只是瞥了眼这孩子,继续向前。巴桑说:“你儿子就是想摸摸马。”张雪没说话,她内心有些羞愧,为什么自己还不如一个牧民懂儿子啊。看着满脸鼻涕的暖阳,张雪有些害怕。这孩子的未来就像眼前的草甸,被埋在黑夜里。
到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停在一个湖边休息。巴桑一直没说话,只是看着湖面发呆。李星听到一连串的爆炸声从远方传来,那里是个巨大的矿场。这一路上,他们路过了几十个这样的露天煤矿。这些天坑袒露在世间,像是死者的眼睛。
张雪来到巴桑身边,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由愣住了。湖水已经干涸,里面落满了尸骨。有鱼的,也有鸟的。密密麻麻,大骨头上摞着小骨头,像是一片雪花。
张雪想起有次问大夫,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得自闭症,为什么如今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得这种病。大夫苦笑着摇头,说主客观原因都有。主观上,可能是父母某一方家族的基因突变导致。客观层面,是因为目前的环境污染很严重。那个时候,张雪还想不明白,臭氧层空洞也罢,南极冰川融化也好,和自己一个小女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暖阳就要遭受不幸。现在她站在天坑边,看着这一地骨骸,好像有些懂了。
天边出现了朝霞,万物披上一层薄薄的金光。新的一天要来了,虫子和小鸟在叫。
咒骂声从远方传来,巴桑循声望去,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宝音正在被几个牧民追赶,他们大喊“站住”“骗子”。有位牧民骑在疾驰的骏马上,用套马杆套住宝音,把他放倒在草地上。牧民们怒骂:“你一点都不像个草原人。”
宝音哇哇叫着,脸憋得通红。受骗牧民举拳想打宝音,巴桑及时拉住了那只握紧的拳头。巴桑问究竟是怎么回事。牧民嚷嚷,三千块买来的手机,怎么摁都摁不亮,打开一看,就是个空壳,里面灌满了沙子。
巴桑脸红了,说:“我赔你。”他踹了一脚宝音,说:“快站起来。”大家望着宝音,眼神憎恶。宝音像看不见,却抬头看天,朝霞铺满了天空。
临走时,那牧民对巴桑说:“巴桑老爹,今天要不是你,我真把宝音揍了。你怎么会有这么不成器的儿子!”
他们走后,巴桑说:“你一个牧民,四处行骗,你是不是不想过了?信誉在草原上比天还重要啊!”宝音踢着草,不争辩,他只是想着自己真是太倒霉了,都逃到了这里,还是被他抓住了。巴桑说:“天天想着去太空,去做宇航员,你就是疯了……”
这时,宝音看到车上有个孩子在好奇地观察自己,故意拉下面巾,露出脸来做怪样。张雪和李星被宝音的模样吓得惊叫,张雪用手遮住了暖阳的眼睛。巴桑狠狠在宝音屁股上踹了一脚,可宝音感觉不到疼痛。这么多年来,他脸上的伤疤奇痒无比,从未消散半分。奇痒夺走了他的痛觉。他甚至为这个恶作剧感到得意。谁也想不到,暖阳扒开了张雪捂着自己眼睛的手,冲着宝音笑了。
宝音感到不可思议,这是他第一次遇到不害怕自己的陌生人。他推开父亲,来到越野车边,打开了车门。他说:“小孩,你笑什么?”张雪通过后视镜看着儿子,她很紧张,生怕宝音伤害他。
暖阳却不说话,只是伸出手来要摸宝音,好像在摸一匹马。宝音躲避不及,暖阳的小手碰到了他的额头。宝音哆嗦了一下,暖阳的小手很温暖,像阳光一样。一只蓝蝴蝶落到了窗边,暖阳的眼睛亮了。宝音轻轻捏住那只蝴蝶,送到暖阳的手里。宝音说:“小孩,我们交个朋友吧!我叫宝音,是个宇航员,快要上太空了。你叫什么?”暖阳只是笑,将蓝蝴蝶放飞回空中。
宝音笑了,摸摸暖阳的脑袋,对目瞪口呆的李星和张雪说:“这孩子格局大,将来能成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