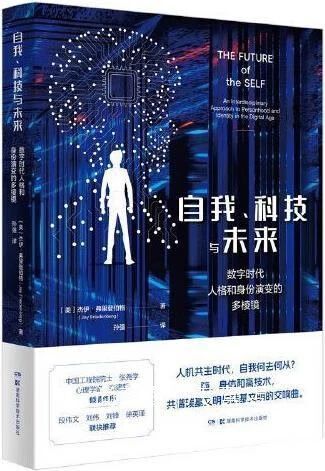
孙强教授将《自我、科技与未来:数字时代人格和身份演变的多棱镜》一书寄来有段时间了。一是此书重要,需要找足够时间空档集中阅读;二是近来工作主要集中于完成《AI性别:日常生活的日常跃迁》一书的初稿,拖到前几天才完工,故而此书读得晚了一些。
“AI时代三部曲”第三本我要讨论“AI与人性”的问题,自我问题必然是重头戏。《自我、科技与未来》读得虽晚,但挺认真,让我对目前自我的新科技研究有了全景式的了解。
此书的作者弗里登伯格是美国的心理学教授,野心很大,试图把既有关于自我的研究成果综述一下,重点是在新科技发展前沿之中加以总结。为什么呢?作为心理学教授,之所以会写此时,当然是因为当代科技尤其是认知科学、人工智能、人类增强等领域的研究者们,近来对自我问题着力甚多,形成大量新的问题、观点和理论。换言之,自我问题在与智能革命吸纳公关的新科技发展中几乎无处不在。
这里所称的“自我问题”,并不仅仅指“什么是自我”的基本界定问题,而是与“自我”相关的问题簇,比如人工意识有无可能、如何建构,化身与自我改造,自我与记忆尤其是自传式记忆的关系,赛博格的自我问题,自由意志有无与限度,延展心灵问题,数字自我与自我障碍,自我与人工记忆,电子游戏的自我影响,思维克隆与数字永生问题等,非常复杂,与智能革命关系非常紧密。显然,随着智能革命的推进,人类的自我观念将发生颠覆性转变。在此背景下,关于自我界定的传统问题——无论是难问题,还是易问题——都不再重要,谋求统一界定的努力也将消失。
当然,就自我的新科技研究正在渐入佳境而言,现在对自我问题进行总结和汇编还不到时候。因此,我觉得,《自我、科技与未来》的诸多观点不必太在意,相反它梳理的各种问题更为有价值。这些问题出现在新科技发展的前沿,影响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和步伐。
无论如何,弗里登伯格做了总结,观点我照录于下:
(1)一个人活整个人类通常被认为是生物物种的成员,而自我或身份是个人人格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来发现我们是谁,或者创造出另一个版本的自己。我们有可能创造出有着独一无二身份的人工人。
(2)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自我的复杂性,包括但不限于历史的、进化的、发展的、文化的、有神论的、哲学的、心理学的和神经科学的方法。
(3)新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自我的理解,相关例子包括脑成像技术、修复术、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纳米技术和基因工程。赛博心理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在帮助我们创造和理解数字自我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4)物质性和科学要求自我是有某种东西构成的,而不是像灵魂那样不可言喻。模式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认为,是系统的关系层面和操作层面构成了自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基质就无关紧要,然后我们可以将自我“上传”到电脑中,在那里它有可能扩展并永远存在。
(5)即使自我可能是不断变化的,但它也必须持续一段时间,能够解释这种持续性的可能是那些有关自我的在时间和空间条件下保持不变的方面。将我们的经历记录下来并能以记忆的方式获取它们,可能有助于感受到一种恒定的自我。数字技术能够使我们更详细地记录和存储我们的生活。重温这些记忆可能会强化或改变一个恒定的自我,但仅凭记忆能否构成自我仍存在争议。
(6)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我们都不知道自我是否需要被限制。脑会根据感官输入来构建我们身体的表征,我们可以操纵这些输入从而让自己相信肢体被拉长了,相信自己的能够拥有原本没有的肢体,甚至相信自己属于另一个身体。利用技术来获取信息可能会将我们的自我延伸到其他设备中。元胞自动机和有感知能力的软件可能不需要中心化的物理学,而是可以作为网络中的程序存在。
(7)很多不同类型的自我是由相互作用的自我组成的,如本我/自我/超我、理想自我/真实自我,以及各种特征的自我。像赛博格、人工智能程序和机器人之类的新的自我形式正在不断涌现,这其中的一些自我可能是“独立的”,与我们分离,但我们可以并将会与自己的创造物融合,来增强我们的自我并转变成全新的自我。
(8)个体的自我或子自我由不同的部分组成。存在着某种普遍共识,人们认为这些部分对应于感知、理性/认知、记忆(包括自传体记忆)、动机、情感、自我觉知、创造力和道德能动性等方面的能力。已经存在能够展示这些能力的计算机程序。自我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主观觉知或意识,创造具有意识到软件或硬件智能体或许是有可能的。
(9)目前还不清楚自我是单一的还是分布式的实体。多数研究人员都认可的观点是,自我包括多个方面,这些方面相互作用,有时聚在一起,有时分开。神经科学的研究工作还没有证实存在任何一种单一的自我系统。脑可能会执行协调行动(比如神经同步)来集中注意力和整合不同的自我。
(10)自我及存在于社会环境中,也存在于物理环境中,并与其他同类相互作用。社交媒体、互联网和其他形式的软件允许我们在网上创造不同版本的自我,以宣传我们的优点,并与他人建立来纳西。游戏中的角色扮演能够使我们演绎新的自我,改变现有的自我,并建立新的关系。
(11)无论是在现实环境中,还是在与软件交互时,自我都可能会出错,有些情况是先有蛋一些问题转移到了数字世界,其他一些问题则是区啊你新年的。像虚拟现实疗法这样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和修复自我的异常。
(12)我们正在步入这样一个未来:我们可能会不断地栖息于自我的数字表征着,而自我的自主表征能够在我们不在场时发挥作用,这些化身将会出现在虚拟世界中,并有可能协调商业和娱乐活动。
这些总结出现在该书的最末尾。
如上所述,我关心自我问题,主要聚焦于智能革命或AI对人性及其观念的冲击上,尤其是担忧“人的机器化”。如此焦虑的前提性认识在于:没有普遍的、一致的、实在的所谓人性,人是可能性或不确定性本身。所以,包括AI在内的新科技才可能从根本处撼动所谓“自我”,使之朝着“人的机器化”方向前进。更为重要的是,“自我认识”或主体观念被彻底颠覆,朝着量化自我、计算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方向急速前进,此即我所谓的“科学人的崛起”。
我需要说清楚的是:在类似无我的理解下,我们如何可能对“人的机器化”进行批判呢?如果人是一种可能性,为什么人不能作为一种智能机器、智能体存在于世呢?人的机器化究竟有什么可怕之处呢?可能的解释是:确定即是罪过,机器化是一种确定的东西。不仅机器化,所有试图确定人、人性、自我的尝试都应该批判。
比如,最近我们提出的“二甲子的人生智慧”的思想,讲的就是人的时间规定性。长期以来,哲学上讲主体分析又称为限定性分析,主要就是因为人在时间上的有限性。可是,有限与有限并不一样。平均三四十岁的人,与平均一百岁的人,还能是一样的可能性或不确定性吗?就有限的阈值上讲,它们必然是不同的。
从主体观念上讲,“人的机器化”根本上否定人类价值观进化的可能。这是智能社会最危险之处,“二甲子的人生智慧”本质上是对当代价值的重估重构。